- · 城市与环境研究版面费是[04/09]
- · 《城市与环境研究》投稿[04/09]
- · 《城市与环境研究》数据[04/09]
- · 《城市与环境研究》期刊[04/09]
侯深谈《无墙之城》与美国城市环境史(2)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讨论环境正义时,不同群体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相对其他人而言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更大,从环境掠夺的财富更多,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讨论环境正义时,不同群体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相对其他人而言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更大,从环境掠夺的财富更多,制造的问题也更多,他们在奴役自然的同时也奴役了其他大部分人。但是,我们还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大部分其他人究竟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一名消费者存在于地球之上的,我们各种层次的消费既包括人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资料的获取,也包括生存之外比如文化层面上的消费。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无辜的,因为毕竟我们接受了资本文化的规训,虽然不是订立规训的人。
侯深:首先,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虽然不是一位城市环境史家,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依然最大,他的研究奠定了我对环境史的整体认识。《无墙之城》的绪论“膨胀的城市,萎缩的大陆”的基调正是建立在他2016年新出版的《萎缩的地球》之上。
我开始构想时还是以地形特征来选择,比方说海滨之城、沙漠之城、平原之城和河流之城,但等到真正思考如何书写的时候,便希望不局限于去写个案城市,而是希望这些特定的个案能延续我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整体考察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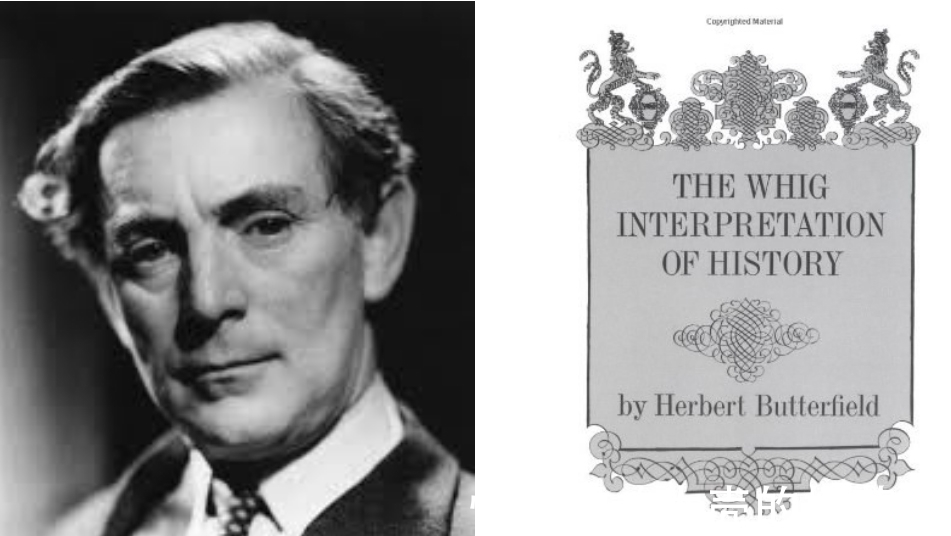
写这本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意外。最早我是想完成《山巅之城》(关于波士顿的环境史研究),因为我在博士论文调研中搜集了大量波士顿的档案材料,所以一开始想做波士顿城市环境史研究。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将对波士顿环境史的研究拓展到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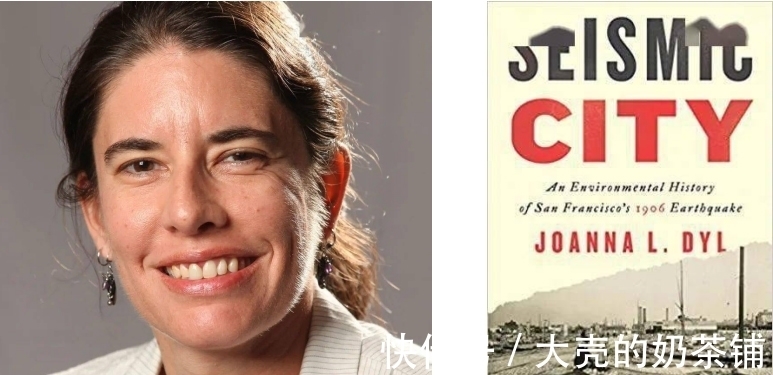
侯深:我们在谈现代史的时候,如果脱离资本主义,就变成无本之木。虽说我们不能把关于环境的讨论都归结于资本主义,但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不去谈它的资本主义扩张,也无法真正地去思考和理解它的城市环境问题。
那么您能否在环境史的语境下定义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它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环境史学者在批评资本导致了城市的扩张和环境衰落时,到底在批评具体何种资本、哪些群体?您如何看到其中的环境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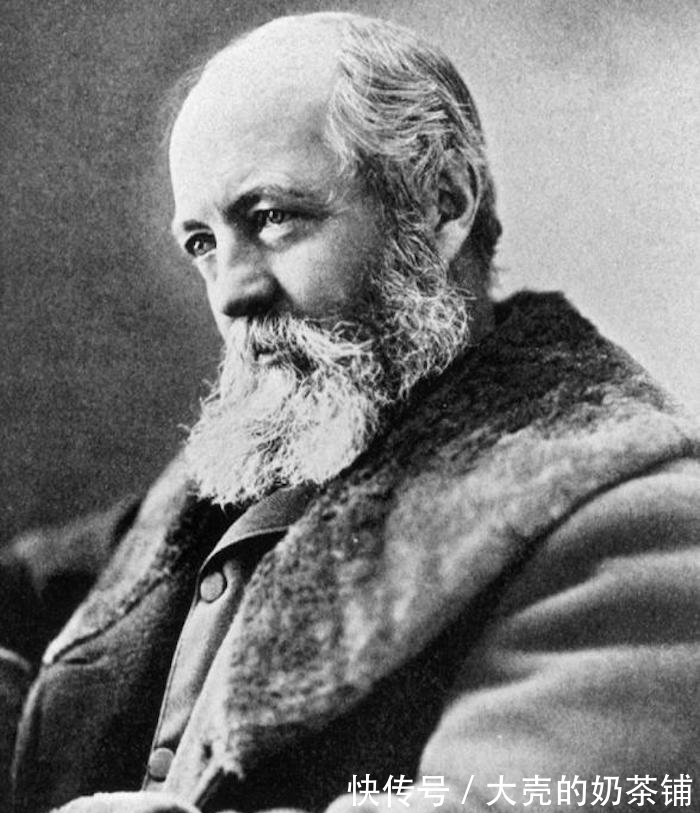
侯深:这只是我的一个构想和尝试。我们在谈演化的生态系统时,并不一定要涵盖自远古而来的演化的生态系统,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演化当中。研究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必须要将其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考虑。在这个层面上,我个人认为我对堪萨斯城的城市环境书写是相对成功的,因为我始终在关注大平原自身的变化如何影响堪萨斯城,堪萨斯城又如何影响大平原。这正是一种系统性的演化。
熟悉环境史学术脉络的人都知道,自从1990年美国环境史学界著名的“圆桌论坛”之后,环境史研究者关于自然和文化的争论似乎也从未停过,那您如何看待对这场持久的争论?
您书中的另外一个核心主题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我从书中看到资本主义并不单是对无限增长的信仰、对自然世界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趋势,还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基础,并对人类与自然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力量。您总结到“城市作为资本权力的中心,既是环境扩张中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能谈谈城市在资本扩张和环境变迁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吗?

美国人在边疆传统中将远足、野营等定义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这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文化影响。中国也有漫长的去山林中间寻找自然的传统,但它没有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潮流,不管是因为财力的原因,还是因为交通的原因。
侯深:这种消费自然的方式其实是新的社会时尚和身份认同的标志。比如跑马拉松一定意义上是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是一个符号。但在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种情感断裂,它造成的是一种深层的渴望。我们都渴望净水,我们渴望洁净的空气,我们渴望美丽的景观——不管这种美丽景观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

侯深:两本书的写作框架是全然不同的:《城市自然化》是一个非常小尺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部微观史(micro-history);《无墙之城》的研究尺度就大了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宏观史(macro-history)。
文章来源:《城市与环境研究》 网址: http://www.csyhjyj.cn/zonghexinwen/2022/0927/1594.html